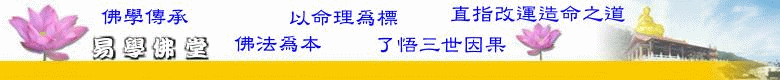道場開了以後,來往的人太多。雲谷禪師又移居到後山的幽深處,叫「天開巖」的山裡修行。依然是影隻形孤。在這一階段,許多官員和在家居士,因為陸公的參與。引導,大家都已知道有「禪宗」這回事。又傳聞雲谷禪師風範,所以很多人去參見他。
凡是來參見的人一到,雲谷禪師總是問他們:「你日常做什麼勾當?」不論貧賤富貴僧侶,到他禪房來。一定把「蒲團」擲在地上,叫他們盤膝正坐。
反觀自己「本來面目」,甚至於整天整夜不說一句話,在臨別的時候,一定叮嚀著說:「你不要浪費歲月啊!」等到再見到的時候。一定要問:「分別後努力修道,功夫用的有沒有進步啊!」所以遇一些無心修道的人,便茫茫然無法回答。因為他的慈悲心愈切而嚴責之情更重。
雖然雲谷禪師沒有建立甚麼門派,收徙傳道,但是見到他的人彷彿面對高峰峻崖。有不寒而慄之感。然而。雲谷禪師全都以平等心來攝受、加被他們;他接引參訪他的人,向來都是低聲婉語,平心靜氣,從沒有過嚴厲的責備。
因而讀書人、為官的人。皈依他的也一天天多起來。因此,他不能靜靜地修行,有人想求見他的,他總以接引他們、加被他們為前提也接見了。每年,他從山中到城裡一次,一定寄單在「回光寺」。........回最前
每次到回光寺,在家男女居士,都湧過來,如圍繞著蓮花寶座一樣,而雲谷禪師看到這種受人擁戴的景況,好像看作夢中的花、霧中的月,不起一點分別心,因此,親近他的人,好像嬰兒依傍慈母一般。
雲谷禪師每次出城,大多寄居在普德寺。寺裡的老和尚懼鶴悅公,實在受到他的益處不少,我(憨山大師自稱)的太師翁(即太師祖)每次請他到方丈室裡來求教,常常是十天半個月的。我做小孩時,便親近侍奉他了,承他老人家非常器重我,對我不厭其勞地訓誨開示。
我十九歲那一年,忽然不想出家了,被雲谷禪師知道了,問我說:「你為什麼要違背最初立志出家的心願呢?」我就說:「祇是我厭煩一般出家人太過庸俗了!」
雲谷禪師說:「你既知道厭煩世俗,又為什麼不學一學古代高僧呢?古代的高僧,皇帝不以臣子的地位看待他;父母不以子女的地位教養他;天龍八部對他無限地恭敬,也不認為可喜:你應該找出「傳燈錄」。「高僧傳」這些書讀讀看,就知道了!」........回最前
我(憨山大師自稱)當下就檢查書箱,查出一部「中峰廣錄」的書,捧著去見雲谷禪師,師說:「你熟讀這部書,就知道出家人的高貴之處了!」
我從此時便決心落髮為僧,實在是受到雲谷禪師的啟示,這是嘉靖(一五六四,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)甲子年的事。
過了兩年,到嘉靖四十五年冬天,雲谷禪師悲憫禪宗將面臨滅絕的地步,就約集了五十三位同道,在「天界寺」結期坐禪,師全力鼓勵我參加共修,指示我參「向上一著」,並且先教我念佛數聲,再反觀這「念佛的人是誰」?到此時我才知道有禪宗這回事。而此時南京各佛教寺院,參禪的人不過四。五個罷了!
師漸漸老了,慈悲心愈為深切,雖然是七、八歲的小沙彌,也一律以慈悲的眼色看待他們,以恭敬心對待他們,凡是平時行住坐臥,沒有一樣不當面懇切地教導。耐心而有條理地指示他們;凡見到這種景象的人,人人都以雲谷禪師對自己特別親切,既然是他的護法心深切,不輕視初發心學佛的人,不怠慢破戒的比丘。........回最前
而當時有些出家人不能遵守戒律,凡是違犯了國家禁令的人,雲谷禪師一旦知道了,不等別人求救,他就自動去救助了,而且一定要懇求主管官吏,說佛法完全付託政府官吏為「外部護法」,祇希望他們能體悟佛陀的心意,對出家人的毀辱,便是對佛陀的毀辱了,聽到這席話的官吏們。
沒有不馬上改變了態度,直到把那些犯戒的人釋放為止。可是,這些事,外界竟然大多不知道,因此聽到這些話的人也不曾因為雲谷禪師的多事而感覺厭煩;時間久了,大家都知道他是出於非親非故,「與自己並無關係的大慈悲心」啊! ........回最前